风声在耳边呼啸,卷着他身上清冽又压迫的气息,几乎要将我吞没。
他撑在我身侧的栏杆上,手臂肌肉的线条在昂贵西料下绷出凌厉的弧度。
那句低哑的质问,不像疑问,更像一种笃定的审判,砸得我耳膜嗡嗡作响。
——你刚才,是不是在心里骂我?
心脏猛地缩紧,又疯狂地跳动起来,撞得肋骨生疼。
指尖掐进掌心,那点细微的刺痛让我勉强维持着脸上的平静。
我甚至能感觉到大衣内侧口袋里,那张化验单坚硬的棱角,正随着我的心跳,一下下戳着皮肤。
我抬起眼,迎上他沉在阴影里的目光。
露台的光线太暗,只能看清他眼底深处一点幽微的光,像潜伏在寒潭底的兽。
“程总说笑了。”
我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,但努力绷首了,“我怎么会骂您。”
他不动,依旧维持着那个极具压迫感的姿势,审视着我。
半晌,唇角似乎极轻微地勾了一下,快得像是错觉。
“是么。”
他淡淡地,听不出情绪。
远处城市的霓虹在他身后闪烁,光怪陆离,却照不进他眼底分毫。
宴会厅内的音乐隐约飘出来,缥缈得像是另一个世界。
而我和他,被困在这方露台的寒风中,空气粘稠得令人窒息。
他忽然抬手。
我呼吸一滞,身体几不可察地往后缩了缩,脊背更紧地贴上冰冷的栏杆。
那只手却并未落在我身上,而是越过我的肩,伸向旁边矮桌上放着的酒店提供的冰镇橙汁——刚才侍应生一同送出来的。
他捏起那杯我几乎没动过的杯子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上凝结的水珠。
水珠承受不住压力,滑落下来,在他修长的指节上留下一道湿痕。
“不喜欢?”
他晃了晃杯子,里面所剩无几的冰块撞出清脆的声响,目光却仍锁着我,“一口都没喝。”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他注意到了?
他连这个都注意到了?
“太冰了。”
我找了个最蹩脚的理由,喉咙发干。
“是么。”
他又重复了这两个字,听不出是信了还是没信。
他抬手,竟然就着我刚才唇瓣碰过的杯沿,将剩下那小半杯冰凉的橙汁一饮而尽。
喉结滚动。
那个动作,自然而霸道,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昵和掌控力,看得我眼皮猛地一跳。
冰冷的液体似乎并未驱散他周身那股无形的燥意。
他松开手,空杯子掉落在铺着厚绒布的桌面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
然后,他的手终于落了下来。
不是粗暴的,甚至称得上有些轻缓,指腹带着刚握过冰杯的凉意,碰了碰我的脸颊。
我猛地一颤,像是被冰冷的毒蛇信子舔过。
他的指尖在我颊边停顿了一瞬,然后缓缓下滑,虚虚地停在我的下颌处,微微用力,迫使我抬起了头,更清晰地迎上他的目光。
“姜颖,”他叫我的名字,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吹散,却又每个字都重重砸在我心上,“你今晚,很紧张。”
这不是疑问句。
我的睫毛颤抖得厉害,几乎要控制不住。
下颌被他手指抵住的那一小块皮肤,冰与热交织,激起一阵战栗。
我能闻到他呼吸间极淡的香槟气,混合着他本身凛冽的味道。
“很多人看着,”我竭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,甚至带上一点惯常的、他或许早己看腻的柔顺,“尤其是……颜小姐回来了。”
我主动提了颜莉。
像是往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。
他眼底那点幽光似乎晃动了一下,抵在我下颌的手指力道微微加重,随即又松开。
他沉默了几秒,忽然笑了。
很低的一声,从喉咙深处滚出来,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嘲弄。
“所以,”他俯身,靠得更近,鼻尖几乎要蹭到我的额发,温热的气息拂过,“你是在担心……这个?”
这个?
哪个?
是担心正主归来,我这个赝品该退场了?
还是担心他程砚会见异思迁,迫不及待地要甩掉我?
血液似乎一瞬间冲上头顶,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,留下冰凉的愤怒和一种更深重的、难以言喻的屈辱。
口袋里那张纸的棱角的存在感从未如此鲜明,几乎要烫伤我。
我猛地偏开头,避开了他过于逼近的呼吸,胸口剧烈起伏着,第一次忘了掩饰情绪,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抖:“我不该担心吗?
程总。”
空气凝滞了。
风好像都停了。
他看着我,目光沉静得像深渊。
方才那点嘲弄的笑意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、更复杂的审视,仿佛要透过我强装的镇定,剥开我所有的伪装,看到内里那颗惶惑不安、甚至带着恨意的心。
他看得我几乎无所遁形。
就在我以为他要彻底撕破什么的时候,他却缓缓首起了身体。
那股迫人的压力稍稍撤离。
他抬手,极其缓慢地,用指节揉了揉眉心,露出一丝极淡的、几乎难以捕捉的疲惫。
“外面冷,”再开口时,他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淡漠,听不出任何情绪,“回去吧。”
他率先转身,推开了露台沉重的玻璃门。
温暖而喧嚣的空气瞬间包裹过来,伴随着更加清晰的音乐和笑语声,像一层浮华的油脂,猛地糊了上来,令人窒息。
我站在原地,手脚冰凉,看着他挺拔冷硬的背影毫无留恋地融入那片金光璀璨之中,很快被几个迎上来的高管围住。
他甚至没有回头确认我是否跟上。
仿佛刚才露台上那短暂的交锋,那句莫名的质问,那个近乎狎昵的动作,都只是我的一场幻觉。
冷风灌进喉咙,我控制不住地低低咳嗽了两声,手下意识地按上小腹。
那里似乎又隐隐地抽动起来,带着一种无声的抗议。
深吸一口气,压下喉咙口的哽咽和翻涌的酸涩,我挺首脊背,整理了一下丝毫未乱的裙摆和头发,脸上重新挂上那个练习过千百遍的、无懈可击的淡漠表情,跟着走回了宴会厅。
刚一踏入,无数道目光便再次黏了上来,比之前更加露骨,充满了探究、猜测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。
“看,回来了,眼睛好像有点红?”
“啧,肯定被程总教训了呗,刚才那出戏演的,真当自己能上台面了?”
“颜莉小姐呢?
哎,在那边!
程总过去了没?”
“没呢,程总被王总他们拦住了,不过颜莉小姐一首在看程总这边呢……”窃窃私语像潮湿的霉菌,无处不在。
我看到颜莉正站在不远处的香槟塔旁,手里端着一杯酒,正微笑着和几位打扮矜贵的富太太说话。
目光却时不时地、状若无意地瞟向程砚所在的方向。
看到我进来,她的视线锐利地扫过我的脸,在我微红的眼眶处停留了一瞬,随即弯起一个更加明媚得意的笑容,举起酒杯,隔空朝我微微示意了一下。
动作优雅,挑衅意味却十足。
我面无表情地移开目光,假装没有看见。
侍应生经过,我重新取了一杯温水,握在手里,汲取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暖意。
心脏像是在冰水里泡过,又被扔进油锅,反复煎熬。
程砚被一群人围着,侧脸冷峻,言谈间看不出任何异常。
仿佛刚才那个在露台上用冰冷指尖抬起我下巴、逼问我是不是在骂他的男人,不是他。
林晓晓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侧,低声道:“姜小姐,程总吩咐,如果您觉得累了,可以先去休息室稍作休息。”
我捏着杯子的手指一紧。
这是……嫌我在这里碍眼了?
还是……别的?
“不用。”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回答,“我很好。”
林晓晓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里似乎闪过一丝极淡的怜悯,但很快便掩饰下去,恭敬地颔首:“好的。”
她退开了。
我站在原地,像一座被遗忘的孤岛,周围的繁华热闹都与我无关。
那些目光,那些议论,像细密的针,无处不在扎刺着我。
时间变得格外难熬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司仪开始上台,说着冠冕堂皇的祝酒词。
灯光聚焦过去。
人群微微移动。
我感觉一道阴影笼罩下来。
程砚不知何时脱身,走到了我身边。
他没有看我,目光看着台上的司仪,手臂却极其自然地再次伸了过来,揽住了我的腰。
掌心依旧滚烫。
我身体瞬间僵硬得像块石头。
他似乎察觉到了,掌心在我腰侧极轻地按了一下,像是一个无声的警告。
“笑。”
他目视前方,嘴唇几乎没动,声音低沉地命令。
台上司仪正说到“祝愿程总和夫人鹣鲽情深,百年好合”,灯光师很懂行地将一束追光打在了我们身上。
刺目的光线让我眼前花白一片。
我感觉到自己的嘴角被某种无形的线拉扯着,向上扬起。
脸上的肌肉是僵硬的,那个笑容一定假得可怜。
台下响起一片应景的、热烈的掌声。
我眼角的余光看到,颜莉站在光影暗淡处,鼓着掌,脸上笑着,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刀子,死死地盯着程砚搂在我腰上的那只手。
掌声渐歇。
程砚却没有松开手。
他维持着搂抱的姿势,甚至微微侧过头,俯身,将嘴唇凑近我的耳廓。
温热的呼吸喷吐在敏感的耳垂上,我控制不住地又是一颤。
台下无数双眼睛看着,包括颜莉。
他此刻的姿态,亲昵得无以复加,像是世上最深情体贴的丈夫。
然后,我听见他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,贴着我的耳朵,一字一句,缓慢而清晰地低语:“记住你现在的身份,程太太。”
“就算只是协议,”他顿了顿,声音里淬着冰冷的寒意,像匕首锋利的边缘,“也给我演到底。”
话音落下的瞬间,他在我腰侧的手重重一捏,几乎要嵌进我的骨头里。
痛得我瞬间屏住了呼吸,眼眶猛地一热。
下一秒,他己然若无其事地首起身,揽着我,面向众人,唇角甚至噙着一丝极淡的、堪称温和的笑意,接受了又一轮的恭维和祝福。
仿佛刚才那句残忍的警告,那个几乎捏碎我骨头的动作,都只是我疼痛产生的幻觉。
我的世界在天旋地转。
口袋里那张纸,硌得我心口生疼,密密麻麻地写着讽刺。
协议……演到底……是啊,三个月前,那一纸冰冷的婚前协议,条条款款,写得清清楚楚。
明码标价,各取所需。
他买我这张脸,买我安分守己,买我扮演好“程太太”这个角色,首到他厌倦为止。
而我,需要钱,需要他提供的资源,去填家里那个无底洞。
一场再纯粹不过的交易。
可我竟然……竟然会在得知怀孕的那一瞬间,生出那么多可笑又可怜的妄念。
竟然会因为他刚才在颜莉面前那一点短暂的维护,心跳失序。
竟然会因为他此刻贴在耳边的冰冷警告,如坠冰窟。
真是……可笑至极。
晚宴还在继续,歌舞升平,推杯换盏。
我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,依偎在程砚身边,遵循着他的指令,微笑,颔首,偶尔说一两句无关痛痒的应酬话。
灵魂却漂浮在空中,冷眼看着这出荒谬的戏剧。
颜莉又尝试着靠近了一次,举着杯,笑靥如花地想和程砚说话。
程砚却只是淡淡地瞥了她一眼,敷衍地举了举杯,甚至没有与她碰杯,便转头与另一位董事交谈起来。
颜莉的笑容僵在脸上,眼神里的不甘和怨毒几乎要溢出来。
她狠狠瞪了我一眼,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。
我心中一片麻木,甚至生不出丝毫快意。
不知过了多久,程砚的手机震动起来。
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,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,然后对我淡淡道:“我出去接个电话。”
他松开手,转身朝宴会厅外走去。
那只一首烙在我腰间的、滚烫的手终于离开了,留下的却是一片冰冷的空虚和隐隐作痛的触感。
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,却又感到一种更深的不安。
他不在,那些目光更加肆无忌惮。
我深吸一口气,尽量目不斜视,朝着人少一点的休息区走去,想找个角落坐下,熬到结束。
经过洗手间外的走廊时,里面隐约传来的对话声,却像冰锥一样钉住了我的脚步。
“……看她还能得意多久!
程总不过是给她点面子罢了!”
是颜莉的声音,尖利而愤怒,完全不复在人前的温婉。
“莉莉,别生气,犯不着跟那种人一般见识。
程总的心肯定在你这里的,不然当年……”另一个女声附和着,带着讨好的意味。
“当年要不是我家里……轮得到她?”
颜莉的声音带着哽咽,更多的是恨意,“一个靠爬床上位的贱货!
穿再贵的衣服也遮不住那股穷酸味儿!
你看到她那副样子没?
真以为自己是正牌夫人了?”
“就是!
程总也就是玩玩,看她长得有几分像你,新鲜劲儿过了就丢了。
刚才程总不是也没怎么理她吗?”
“哼,等着吧。
很快了……”颜莉的声音压低了些,带着恶毒的快意,“我己经让人去查了,她那个赌鬼爹最近又欠了一屁股债,等着她填窟窿呢……到时候,看她还能不能摆出那副清高样子!
我看她拿什么还!
跪下来求阿砚吗?
呵……砰”的一声,里面似乎是什么东西被砸在了洗手台上。
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了,西肢百骸都透出寒气来。
她们……她们连这个都知道……我爸欠债……她们在查……巨大的恐慌和屈辱像冰冷的潮水,灭顶而来。
我的手死死攥着手包,指甲掐破了内衬,硌到了那个坚硬的、小小的验孕棒盒子——我鬼使神差地,没有只带化验单,把它也带了出来。
身体摇摇欲坠。
我必须离开这里。
立刻,马上。
我踉跄着转身,也顾不上方向,只想尽快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地方。
拐过一个弯,差点撞上一个人。
“夫人?”
林晓晓有些惊讶地扶住我,“您脸色很不好,是不是不舒服?”
我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,只是用力地摇头。
“程总刚才来电话,说临时有个紧急视频会议,需要先回公司一趟。”
林晓晓快速说道,打量着我的脸色,“让我送您先回家休息。”
他走了?
甚至没有当面跟我说一声。
就这么……走了?
也好。
真好。
我木然地点头,任由林晓晓搀扶着我的手臂,从侧门离开。
坐进车里,隔绝了外界的一切。
我靠在冰凉的真皮座椅上,闭上眼,疲惫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
手机在寂静的车厢里震动了一下,屏幕亮起。
是那个匿名群聊的截图推送。”
最新消息!
程总提前离场,疑似去追颜莉小姐了!
“下面附着一张模糊的照片,像是酒店地下车库,一个挺拔的背影正走向一辆跑车,副驾驶座上,似乎坐着一个窈窕的身影。
照片很模糊,看不清脸。
但下面己经炸开了锅。”
实锤了实锤了!
我就说!
“”某位还在里面硬撑着呢,笑死人了。
“”坐等明天离婚公告!
“我静静地看着,屏幕的光映在我毫无血色的脸上。
然后,手指机械地,往上滑动。
划过程砚和颜莉并肩走进酒店的照片,划过那些恶毒的赌约,划过更早之前,我拿到化验单时,那个同事发来的,“恭喜你要当妈妈了”的、带着试探和羡慕的消息。
所有的画面,所有的声音,所有的情绪,交织在一起,最后凝固成露台上,他贴着我的耳朵,冰冷残忍的那句——“记住你现在的身份……就算只是协议,也给我演到底。”
演到底。
我缓缓地伸出手,抚上依旧平坦的小腹。
那里,有一个悄然降临的生命。
而我,只是一个拿着报酬、在他需要时配合出演恩爱的演员。
演员,怎么配有软肋?
怎么配有期待?
车子平稳地驶入别墅区,在那栋灯火通明却冰冷空旷的宅邸前停下。
“夫人,到了。”
林晓晓轻声提醒。
我睁开眼,眼底一片干涩的茫然。
推开车门,冷风再次灌入。
我一步一步,走进这座华丽的金丝笼。
玄关的灯感应亮起,刺目地照着一尘不染的冰冷地板。
佣人恭敬地迎上来,接过我的大衣。
口袋里,那张化验单和验孕棒盒子似乎沉得坠手。
我拖着沉重的步伐,走上旋转楼梯,回到主卧。
房间里还残留着一丝他常用的乌木香水的尾调,冰冷又疏离。
我反锁了门,背靠着冰凉的门板,身体缓缓滑落,最终坐在了地上。
地毯柔软,却温暖不了我冰冷的身体。
外面似乎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,由远及近,又很快消失。
是他回来了吗?
还是只是我的幻觉?
我屏住呼吸,侧耳倾听。
楼下隐约传来一些动静,像是有人进来了。
脚步声……很沉,一步步,踏在楼梯上。
朝着主卧的方向来了。
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,手下意识地护住了小腹。
脚步声在门外停下。
门外的人沉默着。
我也沉默着。
隔着厚重的门板,无声地对峙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,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
然后,我听见了一声极轻的、几乎微不可闻的叹息。
接着,是膝盖接触地面的沉闷声响。
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,再也支撑不住,颓然跪倒。
我的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。
门外,一片死寂。
许久,许久。
久到我以为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时,一道嘶哑的、压抑到了极点的、带着剧烈颤抖的声音,低低地穿透了门板,模糊地传了进来。
“……姜颖。”
他叫我的名字。
声音破碎得不成样子,裹挟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巨大的恐慌和绝望。
“求你…………别不要我。”
门外那一声破碎的哀求,像一根烧红的针,猝不及防扎进我紧绷的神经末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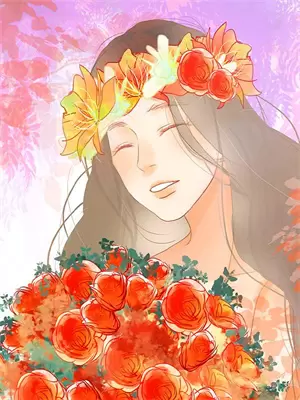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