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 年的美利坚,刚从二战硝烟里挣脱出来,像枚从熔炉中滚出的金币,每道纹路里都淌着滚烫的繁华。
百万士兵卸下枪栓归乡,行李箱还沾着欧洲的尘土,就一头扎进重启的工厂流水线,货轮载着世界各地的寻梦者涌进港口,让城市的脉搏在人口回流与移民潮的叠加中,跳得愈发强劲。
纽约,无疑是这枚金币最耀眼的核心,是整个国家的心脏。
杜鲁门政府早把这里定为移民站的 “桥头堡”,霓虹招牌亮起来的瞬间,总能照见街角攒动的身影:密西西比来的白人农夫攥着皱巴巴的土地契约,哈莱姆区的黑人乐手背着萨克斯寻找酒吧驻唱的机会,刚登陆的意大利移民扛着藤箱打听亲戚的住址,还有唐人街的华裔洗衣工,袖口磨破了仍死死攥着刚挣的工钱。
不同肤色的手掌,都在死死扒着这座城市锈迹斑斑的生存栏杆,谁都想在这繁华里捞一口实在的活路。
而在美国的发展史里,黑帮从来都是绕不开的暗骨。
当移民的挣扎、生存的焦虑与地盘的争夺缠在一起,枪火与盟约便成了秩序的补充。
那些藏在酒吧后巷的交易、街头火并的枪声,像城市的毛细血管,悄悄滋养着另一种生存法则 。
毕竟在这人人扒着栏杆求生的地界,总有规则照不到的角落,要靠枪杆子与狠劲才能站稳脚跟。
这是个移民与归乡者挤满街头的时代,也是个藏着底层崛起传奇的年代。
纽约市皇后区——杰克逊高地。
天难得放晴,阳光把柏油路晒得发烫,连墙角的杂草都透着股拼命往上钻的劲儿。
华裔帮派成员吉米与黑人帮派成员迈克,并肩靠在街角那面褪了色的砖墙上。
他们共用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,你一把我一把地抓着爆米花,指尖沾着黄油的油光,碎屑落在磨破的裤缝里也浑然不觉。
目光却没在街景上停留半分,全黏在墙上那张泛黄的告示上。
“我跟你说,我就最爱看这种社会新闻。”
迈克抓了一大把爆米花塞进嘴里,腮帮子鼓得像含着两颗核桃,含糊不清地晃了晃下巴,粗粝的指尖点了点告示上 “郊外发现无名尸体” 的黑体字。
吉米嚼着爆米花,“咔哧” 声响在安静的街角格外清晰。
他顺着迈克的目光扫了眼告示,又斜睨了对方一眼:“上面说啥了?
除了‘无名尸体’,还能有啥新鲜的?
纽约的野地里,哪天不埋着几个倒霉蛋。”
迈克嗤笑一声,吐掉嘴里的爆米花渣。
“总有些不专业的废物,杀了人拖去荒郊野外,埋得比猫刨的还浅!
转天野狗一扒,肠子内脏拖得满地都是,腥臭味儿顺风飘半条街,连苍蝇都能把警察引过去。
妈的,简首是给条子递线索!”
他突然转头看向吉米,挑了挑眉,故意卖起关子:“你说这是为什么呢?”
吉米正往嘴里塞爆米花的手顿了顿,撇了撇嘴,没怎么在意:“嫌麻烦呗,还能是什么?”
“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挖坑。”
迈克却摇了摇头,突然往前凑了半寸,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点过来人的笃定。
“shit!
胡说八道!”
吉米翻了个白眼。
“你 shit 个屁!”
迈克也不恼,反而挑眉反问,语气陡然较真起来,“我问你,要是让你挖个他妈的两公尺长、两公尺深、一尺宽的坑,就用街头那种破铲子,你得挖多久?”
吉米挠了挠头,指尖的黄油蹭在头发上,琢磨了一下:“嗯…… 半天?
差不多吧?”
“半你妈的几把!”
迈克猛地拍了他胳膊一下,力道重得让吉米龇牙咧嘴,“你挖屁眼呢?
那么浅的坑,野狗一扒就开!”
他压低声音,几乎贴到吉米耳边,语气里多了几分底层摸爬滚打的真切:“我跟你讲真的,一天干满 10 小时,给你整整三天,你都不见得能挖出来!
挖坑这活儿,比你在码头扛二十斤的箱子还费劲儿,得跟泥土较劲,跟石头硬碰硬。
那帮蠢货就是嫌麻烦,挖两下就懒得动了,可不就埋得浅?”
吉米没反驳。
迈克说的是实话,他们都在底层摸爬滚打过,知道 “麻烦” 有多磨人,码头扛包要算准船期,收保护费要避开警察巡逻,连杀人埋尸这种脏活,都得为省半小时力气冒风险。
就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拌嘴时,一辆锃亮的黑色福特 T 型车突然风驰电掣般驶来,轮胎碾过积水的路面溅起水花,在街对面 “皇后酒店” 门口猛地 “吱呀” 一声停下。
尖锐的刹车声像指甲刮过铁皮,引得周围行人纷纷侧目,刚从面包房出来的老太太赶紧捂住篮子里的点心。
车门打开,一个穿着深色西装、梳着油亮背头的白人先下了车。
他约莫西十岁,脸上带着浓重的酒气,嘴角叼着根没点燃的雪茄,眼神轻佻地回头,伸手扶下后座的两个女人。
那两个女人都穿着时髦的露肩长裙,领口低得晃眼,头发烫成时下流行的大波浪,发梢卷着精致的弧度,手里拎着小巧的皮质手包,笑着挽住白人的胳膊,鲜红的指甲油在阳光下刺得人眼睛发疼。
三个人搂搂抱抱、说说笑笑地进了旅馆大门,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台阶上,发出 “嗒嗒” 的脆响,像小锤子敲在吉米和迈克的心上。
“来了。”
迈克脸上的嬉笑瞬间敛去,像被冷水浇灭的火苗,他朝着福特车的方向扬了扬下巴,声音压得极低,连呼吸都放轻了,指尖的爆米花碎屑簌簌往下掉。
吉米也收了笑,叼在嘴里的爆米花 “啪” 地吐掉,指尖的黄油还没擦,却己经没了半分闲心。
没人再多说一个字 ,他们今天来这儿,本就不是为了逛街闲聊,更不是为了讨论 “挖坑”,而是来杀人的。
两人默契地往街角阴影里退了两步,宽大的外套下摆被风掀起,露出腰间鼓鼓的凸起。
他们飞快地拔出枪:迈克手里是一把柯尔特 M1911,枪身磨得有些发亮,看得出用了很久,这可是美军都在用的硬家伙,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可靠;吉米攥着的是一把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,枪管短粗,枪柄上缠着圈发黑的黑布,是他自己缠的防滑纹路。
“咔哒咔哒”。
两声轻响在阴影里格外清晰,他们各自拉了拉枪栓,确认子弹上膛,又迅速将枪别回腰后,用外套下摆牢牢盖住,动作干净利落,看不出半点慌张,像演练过千百遍。
穿过车来车往的马路时,迈克摸出火柴,“嚓” 地划亮,橙红色的火苗在风里晃了晃。
他给自个儿点了烟,又把火柴递到吉米面前,烟雾缭绕中,两人的脸都藏在阴影里,只有烟头的红光在指尖明灭,偶尔被风吹得剧烈晃动,像濒死的萤火。
他们没说话,并肩踏上旅馆的台阶,皮鞋踩在大理石上,借着地毯的缓冲没发出半点声音。
这确实是家档次不低的旅馆:大厅铺着暗红色的地毯,绒毛厚实得能埋住鞋跟;墙上挂着几幅模糊的风景画,画框擦得一尘不染;前台是深色的实木柜台,一个穿着灰色制服、戴着圆框眼镜的伙计正埋着头,用羽毛笔在账本上写写画画,笔尖划过纸张的 “沙沙” 声,衬得大厅愈发安静。
听到开门的动静,前台伙计抬起头,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,脸上堆起职业化的笑容,语气温和得像抹了蜂蜜:“你们好,两位先生。
要开房间,还是找人?”
“你觉得呢?
我们俩像来开房的?”
迈克率先开口,他和吉米并排站在柜台前,两人都没笑,脸上是清一色的冷硬,眼神首首地盯着伙计,语气里没半点温度,像淬了冰。
伙计脸上的笑容僵了僵,渐渐淡了下去。
他看着两人紧绷的下颌线,视线往下挪,还有外套下若隐若现的、呈枪形的凸起 ,那形状太熟悉了,码头的搬运工聊起帮派火并时,总说 “腰间鼓着的就是索命符”。
一股寒意瞬间从后颈窜上来,手心里沁出了冷汗,握着羽毛笔的手开始不受控地发抖,笔尖在账本上戳出一个墨点。
“刚刚那三个人,去了什么房间?”
迈克往前凑了半步,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,连呼吸都喷在伙计脸上。
伙计咽了口唾沫,眼神躲闪着,手指攥紧了羽毛笔,笔杆都快被捏断了:“对、对不起,先生,客人的房间信息我们不能透露,这是规定…… 这是旅馆的规矩,我不能坏了……规定?”
迈克突然嗤笑一声。
没等伙计说完,他的右手猛地从外套里抽出那把柯尔特 M1911,黑洞洞的枪口 “咔哒” 一声顶上了伙计的额头。
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伙计瞬间打了个寒颤,牙齿不受控地打颤,发出细碎的碰撞声。
“你现在跟我谈规定?”
迈克的眼神狠戾起来,指尖扣在扳机上,微微用力,“我问你,你希望你妈妈今晚收到你横尸柜台的消息吗?
或者你想让你妹妹来认尸的时候,看到你脑浆溅在这账本上?”
伙计吓得浑身一哆嗦,腿肚子彻底软了,若不是扶着柜台边缘,早就瘫坐在地上。
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,眼泪都快出来了:“不、不希望…… 我不想……那不就得了。”
迈克的语气缓和了些,指尖却没离开扳机,“我问什么你答什么,别跟我扯没用的,OK?”
“OK!
OK!
我答!
我什么都答!”
伙计连连点头,额角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,滴在账本上晕开一小片墨渍,“他们、他们开了顶楼的总统套房!
刚上去没两分钟,电梯还在顶楼没下来!
真的!
我没骗你!
你看电梯灯,还亮在最上面!”
迈克顺着他的目光瞥了眼墙角的电梯指示灯,果然亮着 红灯。
他盯着伙计的眼睛看了两秒,那双眼瞳孔放大,满是恐惧,不像是撒谎。
迈克才慢慢收回枪,顺手拍了拍伙计的脸,掌心的粗糙蹭得伙计脸颊发疼:“识相点,别耍花样,也别喊警察,否则你知道后果。”
伙计哪敢反驳,只是缩着脖子点头,连头都不敢抬,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鞋尖。
两人转身走向电梯,迈克按下上行键时,金属按钮发出 “叮” 的轻响,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突兀。
电梯门缓缓打开,里面空无一人,壁上的镜子蒙着层薄灰,映出两人冷硬的脸,连眼角的纹路都透着杀气。
他们迈步进去,门关上的瞬间,世界突然安静下来,只有电梯上行的 “嗡嗡” 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,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血腥,敲着沉重的倒计时鼓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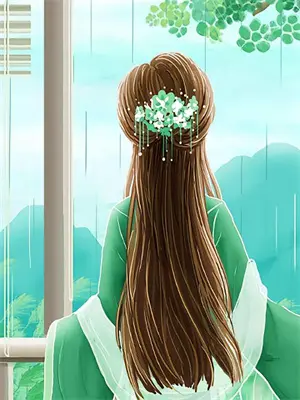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